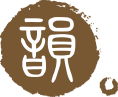今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是评弹艺术大师蒋月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。时近冬至,作为他的门生,我们深切思念恩师当年他驾驶着摩托车风驰电掣的伟岸身影,以及那高雅凝练、幽默含蓄的说表,声情并茂、悦耳动听的弹唱,又一次清晰的浮现在我们的眼前。
实现拜师心愿
他创造的蒋调,受到同行和广大听众的称赞,成为评弹曲调中传唱最广、影响最大的流派唱腔。1983年2月2日,是我们终身难忘的日子,恩师专程从上海来杭州,收我们为蒋门入室的弟子。这一天又恰逢大雪纷飞,让恩师觉得十分开心,因为他喜欢雪景。我们陪同恩师到西湖赏雪,他指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说:“瑞雪兆丰年,是我们师生的好兆头。”
拜蒋月泉先生为师,是我们许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。恩师能收我们为徒,也是机遇和缘分所致。说机遇,是苏州评弹学校和上海评弹团的领导给我们创造的。1982年10月30日至11月23日,苏州评弹学校举办了一期评弹集训班,邀请上海评弹团的蒋月泉、张鉴庭、姚荫梅、唐耿良等多位老一辈艺术家当辅导老师。由江浙沪地区11个评弹团选送的21位优秀中年演员参加了这次集训,我们有幸添列其中,有了一个十分难得的与蒋月泉老师近距离接触和聆听学习的机会。也许是我们与蒋先生有缘分。当时,集训班要求每一档学员向老师们汇报一回三刻钟的长篇折子书,让老师们了解每个学员的基本功水平。我们为这三刻钟的汇报着实下了一番功夫,争取给老师们留下一个好印象。
集训班还委派石文磊、陸雁华两位大姐为联络员,帮助学员与老师们沟通学习中的情况。当时,我们对蒋先生怀着发自内心的崇拜和痴迷,由聪慧伶俐的石文磊大姐所察觉,随即与陆雁华大姐商量,她俩建议我们何不大胆地向蒋先生提出拜师的请求,并愿意为我们塔桥铺路,充当拜师介绍人。
正是由于两位大姐的热情相助,使我们真诚的心愿得到了蒋先生的认可。但是做事作风一贯认真的蒋先生提出了三点要求:一是必须征得双方团领导同意,二是必须征得江苏省曲艺团曹啸君先生的同意(因为我们已是曹先生的入室弟子),三是拜师仪式不允许办酒铺张。
首先上海评弹团吴宗锡团长和浙江省曲艺团领导表示支持,第一个要求顺利通过。但是第二个要求却让我们感到十分为难,怎么向曹先生开口呢?哪里知道,曹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风度,他亲笔写信给蒋先生表示同意,此事让我们感慨万分,再一次领略了艺术家们都是一心为艺,不计较其他的。遵照蒋先生的要求,在浙江省曲艺团团部五楼可容纳300多人的排练厅内,举办了一个既热闹隆重又不铺张浪费的拜师仪式。那天来了好多领导和同仁,蒋先生显得非常高兴。在拜师仪式上,师兄王柏荫同时收了两个女学生,我们也收陈秋影为徒。电视、报纸都做了突出报道,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
事后,恩师在给我们的亲笔信上说:“这次举行拜师仪式的确是件盛事,以后可传为佳话了。”恩师还特意为我们取了艺名,按恩师收的徒弟都为“荫”字辈,朱良欣艺名为朱良荫,周剑英艺名为周剑荫。改名之事,我们请示团里的领导和省文化局领导。领导们经过研究,认为不改为好。仪式因为我们两人经常要为中央首长陈云和叶剑英演出,有一次叶帅对周剑英开玩笑说:“我叫叶剑英,你叫周剑英,巧了!名字相同有缘。哈哈,我是大剑英,你是小剑英······”,二是团里领导认为我们当时已在团里挑大梁,外面有影响了,不改为妥。对此我征求恩师的意见,恩师也同意。我们想,只要牢记自已是“荫”字辈就可以了。
提高艺术水平
拜师后,我们曾请示恩师想学他的书。我们已经向曹啸君先生学过长篇《白蛇传》和《梅花梦》,曹先生的《白蛇》是传统老《白蛇》,而恩师的《白蛇》仿佛是新型盆景,都是新编的一段段折子书,从唱词到唱腔都经过精心设计,花过一番心血的。恩师建议我们“将新、老《白蛇》取长朴短,融为一体”,成为一部更为全面、完整的新编《白蛇传》。
恩师知道我们当时已经着手在搞长篇历史题材《慈禧西太后》的脚本创作,十分支持,鼓励我们下决心把此书攻下来。当时晚报上正好刊登故事连载《李莲英外传》,恩师不厌其烦,每天细心地将报上的连载剪下来,连续剪了30多天,然后装订成册,邮寄给我们作参考资料。在老师的鼓励下,我们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新书的创作中。整整一个夏天,每天泡在浙江图书馆里查找资料,从早晨等开门直到傍晚关门。在上海七宝书场演出时,为了编书、排书、背书,连去食堂买饭菜的时间都节省掉,连续吃了半个月方便面。最终,我们总算把《慈禧西太后》演出本搞成,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。
1983年,我们团试点搞承包,要给演员断奶。当时我们正在排新书,心中没有底,害怕承包后连饭钱也挣不出来,恩师知道后,极力鼓励我们大胆参与。他认为评弹需要不断创新,搞新东西不会没饭吃,有了新书不妨到码头上去锤炼,好书是不断磨出来的。
1983年11月15日,恩师在常熟为第三期中青年评弹讲习班授课,当时我们正好在常熟春来书场演出。恩师得知后,在百忙之中到书场听我们的书,又到后台提出他的看法和改进的建议。他讲得十分具体,一个细节、一句唱词、一个小腔,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作分析,直到我们心中不忍请他休息为止。
1984年6月,恩师在上海举办“书壇生涯50周年纪念演出”,要我们参加演出,我们当然义不容辞,但是恩师指定我们必须演他的长篇现代书《夺印》中的对唱《夜访》。这回书恩师根据他对书中内容的理解,已经将原来的唱词和唱腔做了很大的改动,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跟着录音带重新学唱,无疑是非常棘手的。而且恩师对艺术的要求从来都是十分严格的,我们学好了,必须先唱给恩师听。他认可后方能登台演出。我们不得不格外用心,尽最大努力将《夜访》学好,然后到恩师家中唱给他听,经过恩师的再三指导,终于得到了他的认可。
纪念演出的最后一场,我们的出场次序在上半场最后一刻,这是非常好的档口,场内十分安静有利于演员发挥,而且唱完后正好是中场休息,听众在休息时会评头品足,因此影响也相对大一些。但是在开场前,一位同台演出的演员临时私自提出与他调换档口,让我们把这一档换给他唱,他的档口是中场休息过后的第一档,此时观众陆续进场,闹哄哄的比较乱,演出的效果会差一些。正在一旁的苏毓荫当即站出来制止,说这是蒋先生的安排,不能私自调换,不想这位演员与苏毓荫吵了起来。我们考虑到吵闹后会影响演出效果,想顾全大局,安定大家的情绪,于是主动上前相劝,平息事态。恩师后来知道了此事,特意给我们说:“你们帮我演出,我是很感谢的,这次机会难得,你们那么好,积极支持,又不争名利,我很感动,使我容易安排。我是不善于做联系和安排档子的事,如果你们不随和,我困难更大了,这就是像个师生之谊,我是很感激和很感动的”。
新型师生关系
恩师为人处事谨慎谦虚,有一次陈云老首长来杭州,我们去演出时,老首长说“你们先生蒋月泉是说新唱新的带头人,特别是现代中篇。”我们写信向恩师报告了此事,恩师在回信中说:“老首长关心评弹,点了我的名,这是评弹界的光荣,我工作没做好今后补上吧,对我是督促鞭策,牢牢记住我是评弹的光荣,我要谨慎,如看到我有不对的地方,不要客气,要提醒我,我们的师生是最新型的,这才是新的关系,真正的关系好!”
几年里,恩师写给我们的书信有几十封,我们将它视为珍宝,都一直珍藏着。后来恩师与师母朱若英女士结合,去香港定居,通信才逐渐减少了。
1999年,恩师再次因病来到华东医院,我们去看望时,见恩师已是骨瘦如柴,恩师见到我们坚持让他的女儿梅玲扶他坐在靠椅上语重心长地说:“长远勿见了,都好吗”,梅玲姐说:“爸爸今朝看见你们特别开心,已许久未有笑容了。”此时恩师的双脚有些发抖,他说膝盖冷酸痛,剑英立刻跪到地上用手为为恩师按摩,直到恩师的双膝发热,感到舒服,又觉得过意不去,硬要剑英起来,这是我们与恩师见到的最后一面。
恩师在世时教导我们:“刻苦钻研更上一层楼,成为评弹阵营第一流!”。我们永远铭记在心,作为座右铭,用来鞭策自己、对照自己,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在退休之前,已将上、下两集新编长篇弹词《慈禧西太后》全部创作完成,以此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,如今我们已年逾古稀,但一直坚持边演唱边教学生,这也是对恩师最好的纪念。
(作者是浙江省评弹团著名演员)